女方志园地
主编荐语
我关注女人与家族的关系是从王馨这里开始的。她的《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以身边人物为主线,沿袭了传统的家族体制和谱牒记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史上,家谱中不记女性;因此,罕见女性关注族谱。我以为王馨是一个例外。不期,由她这里寻开去,发现了近代以来女性记录家族和家乡的大量文字,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个代表,也是开山作。由此引发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和崭新的问题:
——女性与父系的乡土究竟是什么关系?
——女性的家乡记忆留下了哪些不同于传统方志记载的历史印记?
我们将两期连发王馨的文章,试图在她的文字里获得启迪。

王馨,1966年生于陕西清涧县城,现在榆林市政协工作,曾主持编辑文史资料20余辑。散文作品在《中国作家》、《延河》、《延安文学》等报刊发表,出版散文集《秋在室杂记》、《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获冰心散文奖)。
我的故城故人
——在《中国女方志》经验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 / 王馨
图 / 王馨 提供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叫王馨,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曾经在政协机关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十几年。之所以有幸参加今天这个专家学者云集的盛会,皆因为几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小书,书名是《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这本书有幸受到李小江老师的关注,我也因此才有机会了解,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优秀的从事女性研究的群体,他们在女性研究方面的探索、努力、贡献和成就,令人感动,也让人仰慕。
会议时间是宝贵的,我就按照大会发言的提示,围绕“家族信息”方面说两点吧。

王馨在《中国女方志》经验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一、家族信息的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家族长辈的口口相传。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三代八口人的家庭,家里有祖父母,父母,弟弟妹妹,还有父亲最小的妹妹、当时尚没有出嫁的七姑。同院还住着我祖父的侄儿、我的堂伯父一家。
那个年代父母都是早出晚归忙工作,所以我是跟着祖母长大的。
每天晚上当我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我的祖母总是盘着腿坐在我的身边,一边用艾条灸手,一边讲过去的事。
那些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在岁月的尘埃之下封存经年,现在却因为祖母的讲述,如同一幅幅新奇有趣的图画,被串联了起来,生动而鲜活。吸引着我,走进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我要把祖母讲的故事写下来,不要让它再一次被遗忘。
另外一位讲述者是祖母的妯娌、我的二祖母。她晚年从西安回来,也住在我们院子里,她们两人年轻时由婆婆(我的曾祖母)教习,略识些字,读过一点书。
祖父闲时也会讲讲家族的故事,他所知道的家族故事应该更多,遗憾的是,那会儿他还没有退休,而我也不懂得主动去探问。
最近这几年,因为我在书中写了一些家族的故事,所以不止是清涧老家、还有一些出门多年定居天南地北的家族成员,也通过家人联系我,加微信,打电话,跟我讲述他所知道的一些家族故事,希望我能够记录下来。但是,随着老人们的离世,能够说清楚那些过往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基本理清了我们这一支从高祖父开始以下五辈人包括女性的简单情况。祖母、曾祖母、高祖母这些嫁到王家的女性,姑姑、姑奶奶、曾姑奶奶这些王家的女儿,时间跨度近百年,经历了近现代历史的重要阶段,她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信息最少的是高祖母,目前只知道她的姓氏、籍贯、去世原因。她有一个远嫁了的女儿,我的书中《传说中的蕴兰》那一篇就是专门写她的。我从小听祖父母讲他们这位姑姑的故事,如何聪明,如何能干,又是如何刚烈,颇有传奇色彩,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丈夫的后人到清涧寻亲的事,更加深了我对这位曾姑奶奶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不久,她的继子的孙子(她本人没有子女)居然联系到了我,在电话里很激动地给我讲述近百年来他们张家与我们王家的每一次往来,讲述年轻时去清涧跟祖父和父亲见面,还把他的女儿喊来与我视频,末了说要专门来榆林看望叔叔(我父亲)。
放下电话,我仔细推算了一下我与这位不曾谋面的亲戚是怎样的关系?他是我祖父的姑姑的丈夫的曾孙。
他的年龄应该与父亲相仿,却在电话里一口一个“叔叔”地称呼我父亲,实在不由人不感慨。我曾写过一组文章在地方报纸上连载,题目是《那些年,我们的亲戚》。“亲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其中有亲情,有温度,有悲欢离合,有千回百转,有你无法虚构的生动故事。
第二个来源,是地方志书。
清涧县城王家,当地人称“寨山王家”,在清涧县城定居已有数百年,是个有历史渊源的家族,因为家谱已经毁于文革,所以,最开始寻找文字资料时,首选自然是官方的地方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清涧最末一次修志是清代道光年间,《清涧县志》清·道光本《人物志》中记载了家族6位成员,《选举志》中有50余名家族成员的简介。在序和修志名氏里,可以看到,七世祖王汝翼是这部县志的三位参订人之一,另外还有7位家族成员参与了修志校勘工作。
在民国《陕西通志稿》里也查到若干条家族成员的生平简介和事迹。
第三个来源,家族文献资料(包括祖先的著述和参加科举考试的硃卷)。
我写书,写家族故事,最大的收获是影响了整个家族对于祖先文献资料的重视和挖掘。
我的族人提供了两份祖先的科举考试硃卷。一份是咸丰辛酉科陕西乡试硃卷,是六世叔祖王宪曾的硃卷,他于当年中举,第二年中进士。一份是宣统己酉科陕西选拔贡卷,是高祖的堂弟王瀚墀的硃卷,他于当年获陕西选拔第二名,会考一等第四十七名。
从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元年(1909),两份硃卷间隔50年,叔侄两人在硃卷个人简历家庭成员报告中,上至本人的十世祖,下至才出生的孩童,共列清涧寨山王氏家族十余代401人,其中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者249人,授实职约60人,虚衔约30人。含实授二品1人,赠二品4人,三品2人,五品10人。
这两份硃卷,相当于一份简洁版的家谱,从史料性来讲,应该是更严肃准确的。每一代男性家族成员的读书、考试、录用、官职、品阶都有介绍。难得的是,偶尔还会用生动感性的文字来赞美子弟,比如祖父的大哥,被赞“九岁熟读六经,现年十一,住学堂”。只有四岁的祖父,也已列名其中。
遗憾的是,女性的信息非常少。只有自己的祖母、母亲、妻子娘家的姓氏、受封的品阶、以及娘家父兄的官职得以记载,胞姐妹及女儿的夫家也有简单介绍。
这两份硃卷可以用来比照地方志,查找更多的有关家族成员的信息。
我们还找到了文革后家族内仅存两卷的《王氏仁荫堂全集》全本,这部书的石印本刊印于光绪三十年(1904),全书共6卷,868页,是一部集家风家训、史学文学、政论文论于一体的皇皇巨著,其观点见识文笔都堪称经典。作者是王汝梅、王宪曾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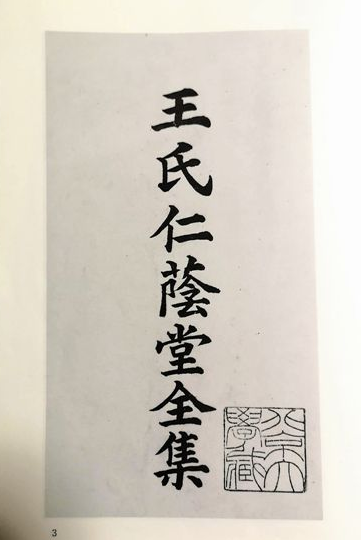
原石印本现存北大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2010年,《王氏仁荫堂全集》被《清代诗文集汇编》全书收录。2015年,《王氏仁荫堂全集》被《清代家集丛刊》全书收录。这是我国首部系统整理的古代家集文献。该书从近千种清代家族文集中精选出150多部汇编而成。全书共201册,《王氏仁荫堂全集》占两册,为第25、26册。
另据县志记载,王汝翼(王汝梅胞弟)著有《荫槐堂文稿》《四书讲义》,藏于乡贤祠待印,后毁于文革。
二、家族信息的整理
对于家族信息的整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被动的潜意识的积累阶段。在成长阶段听长辈讲述,对于家族故事产生了兴趣,对五代以内的亲族关系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甚至还动手绘了一张简图,把其中的人物关系包括姻亲、过继关系都简单梳理出来。
第二个阶段,对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信息回忆并用文字记录的阶段。
成年以后,因为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开始根据回忆整理记录从小听到的一些故事,先后写了《秋在室杂记》《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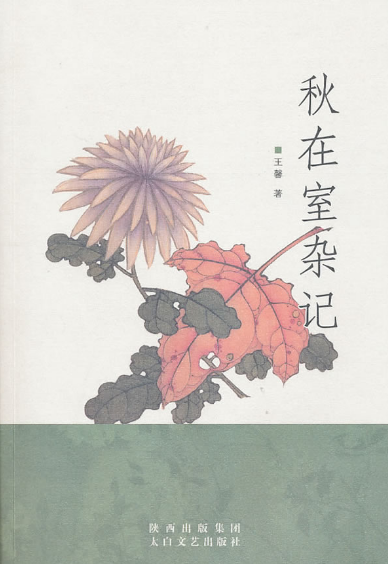
第三个阶段,有目标地收集整理信息,并完成写作计划。
这个阶段,其实是我对自己今后的一个希望吧,希望通过与家族成员的交流沟通,通过对地方志书和家族文献资料的阅读和研究,校勘弥补记忆和口传资料的错误和不足,以此为基础,最终能够写出一本有价值有意义自己也比较满意的书。
那城那水那绵绵的雨
文 / 王馨
城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小县城,那城叫“清涧”,两个水旁的汉字,有水,且清澈,且深幽,很美。
城西有一座山,叫“笔架山”,山势略有起伏,可以歇驻几只大笔,山上松柏郁郁,山下曾有一座书院叫“笔峰书院”。

清涧笔架山,图片来源于网络
小城在唐贞观年间叫“宽州”,到北宋仁宗年间,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来到这里戍边,为防御西夏入侵,他派大将种世衡在宽州故址筑起了一座月牙形的石头城。小城两山夹水,两岸石青,取名“青涧”。
金大宝年间这里开始设置青涧县,沿至明洪武年间,“青涧”改称为“清涧”。
清涧是一座石头城,筑城材料取自当地最著名的特产,一种青色石头。这种石头属页岩,可以整块揭起来做建筑或生活用石材,有首流传甚广的陕北民谣这样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小城的街道自然也是青石板铺就。一两寸厚的石板,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车马,承载着小城的繁华,日子久了,石板会有断裂,城里的大户们会出资修补。
石板街的最后一次大换修工程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一年,一个叫石谦的军人驻防清涧,这个军人后来因为参与领导清涧起义而被载入了史册,但在民间,他是因为重新铺设了小城的石板街而留下了名声。
在清涧,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用整块石板支起来的石桌石床,夏季的时候,白天,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晚上,铺块凉席躺着纳凉、看星星,闲暇时,支根扁担就是乒乓球桌,早些年,一般在清涧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会打乒乓球。
城里的人家集中居住在北关、南坪、东街和寨山,城西便是那条河了,河西便是笔架山。
乾隆十七年,知县吴其琰为县志作序:“顾其地,万山环抱,民皆沟居涧饮,不通商贩,所恃者力田……幸而弦诵遍野,就县试者千二百余人,沿边诸邑,文风首推清涧,明以来登甲乙榜者不绝。”
简洁的文字描绘出一个虽然偏僻封闭却有着深厚的耕读传统的小县。一个当时五万余人口的小县,其中成年男丁只有不足两万人,能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县试,可见其教育的普及程度。

一直到上世纪中期,清涧全县人口也不过二十万左右,县城的老居民是可以板着手指头数过来的。
进了北门,先是王大老爷的宅第,这是一处民国初年的建筑,坐落在高高的石头坡上,他家在清末出过翰林也出过留洋生,所以设计很有特色,几进门楼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的民国风格,看上去很洋气。他家的后代上世纪中期已经迁居海外,只记得有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无声无息地出没在拐角处的小屋里,据说是大老爷的孙媳妇,留下来看家的。其他的房屋,被收归公有,住了一些外姓杂户。头进院子还开办了一家集体企业,是由街道的家庭妇女组成的一家小型丝绸厂,进得大门,石板路两边排着两溜黑色的大瓮,盛着染丝的颜料,院子上方挂着红红绿绿的丝线和丝织品。有段时间,院子里还办了一家鞭炮厂。
我们是同宗。王家迁至小城已有十几代人,祖屋就在城东的寨山上,共七个大院,错落分布于各处。在科举时代,王家曾有一条规矩,子弟没有功名不入家谱,所以人人读书,家业日兴,人称“寨山王家”,在周边名气很大。寨山王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集体定了一个地主成份,族谱被烧毁,已经无从寻根。
县衙也设在寨山上,山上开阔处还屯了官田。
紧挨着大老爷家的是县城另一个有名的惠姓富户,他家的老爷曾当过国民党警察局长,当年共产党打进小城时,编了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进得清涧城,先捉惠华亭……
当年这些人家大多选择了逃离故土,不过,时间证明,他们也不是什么恶霸地主,只是普通的开明富绅,在民间都有积德行善的好口碑。
城里的师家和马家几代经营熟食,配方有家传,做事也厚道,到民国年间也都成为小城里的殷实人家。
小城居民的饮食习惯与周边县邑没有大的区别,以各色面食为主,当地豆类齐全,以豆类做粥做汤做面食也是一大特色。比如“钱钱饭”,是把黄豆黑豆用碾子碾薄成状似铜钱的小圆片,加入小米高粱米和其他豆类,用水煮成的一种稀饭。
清代一个叫郭文熺的曾写《清涧竹枝词》:山城八月已霜天,满目萧条草舍烟。会看街头三日集,儿童争卖饭钱钱。
就此诗看,小城三日一集市的规矩已经有些历史了,并且一直沿袭至今。
小城最特别也最著名的一种小吃是煎饼,因为与各地的煎饼完全不同,所以被人冠名“清涧煎饼”。
煎饼还是老白家的好,那是祖传。他家是我们的邻居,小时候常去观看白家奶奶摊煎饼,那双手非常灵巧,一只小竹片一旋转,铁制的鏊子上便绽开了一张圆圆的洁白的薄饼。煎饼的原料是当地出产的荞麦,先磨成糁子,再人工揉制成汁,最后才上鏊子摊成煎饼。刚摊出的两张煎饼要趁热合成一张,这样每一张煎饼的两面便都有烙花,才能挂住汤汁,才更有味道。汤汁的调制非常关键,虽然用的都是蒜末、姜汁、醋和凉开水,但哪家调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只有老白家是最正宗的,那汤汁,哪个吃煎饼的人都得喝几碗。
小城的方言与周边县邑相差甚远,不出百里,已经是语言不通。汉语拼音中发“j”、“q”、“x”音的字词,小城人统统读作“z”、“c”、“s”,“nv(女)”、“lv(吕)”、“yv(雨)”三个发音,在小城完全同音,而且是一个用今天的汉语拼音已经无法标注的古入声。这样与陕北周边县邑完全不同的发音规律,与江苏某些地区倒有惊人的相似。
邻县人常用清涧方言编些趣话,比如“洗脸”,我们说“思礼”。大家便会开玩笑,清涧人问 “你洗不洗呀?”时,会说“你死不死呀”,外地人吓得落荒而逃。
而“煎饼”二字,小城的人读作“几笔”,后一个字读平声,总是拉了长长的尾音,别有一番韵味,一般外地的人怎么能猜得出这其中的含义呢。
无论是盛夏的夜晚,围在院子石床上乘凉的人们还没散去,还是在腊月天的大雪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话家常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小街的远处传来清亮的叫卖声:“几笔—”,余音不绝,装饰着小城的静夜。
你只要应一声,很快便有左臂挎篮右手提罐的小贩进门,他蹲在地上,先从盖着干净白纱布的竹篮里取出小碗和已经卷好豆腐干的煎饼,再用一只笨笨的木勺从那只黑色的瓷罐里舀出浅茶色的汤汁来……
那才是小城独有的风景。
水
县城的城墙外环绕着一条清澈的河流,说它清澈,决不是说它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透明的水质,而是说它是一条一眼望去有着蓝盈盈的光泽的河流,因为它的河床是整块的光滑的蓝色的石头。
这条河古称溽水,三千年前,周穆王西征路经此地,爱河水清澈且甘甜,曾取水痛饮(《穆天子传》: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想必其时河水汤汤,草木葱茏,是一个温暖且湿润的所在,所以才有“溽水”之名。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溽水俗谓之秀延水。从明朝开始,民间直接称之为清涧河。清涧河发源于清涧西北面的邻县子长,流经清涧,在清涧西南的延川县注入黄河,全长只有168公里。清涧人唤它“大河”,是因为小城还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这条河在县城的南门口汇入清涧河,两条河呈T字形分布,把一个本来就小小的县城隔成几块。这条支流更绢细一些,所以被称作“小河”。
两条河里都长着茂盛的水藻,长长的,柔柔的,随着波光粼粼的流水飘动,像绿色的绸子,像女人们的长发,我们叫它“蛤蟆泥”。水藻里藏着各种各样小小的水生物,只要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有受惊的小蝌蚪小青蛙游出来。
小蝌蚪是孩子们的小玩意儿。清涧河里没有鱼,那时候鱼是不多见的稀罕物。但清浅的河里到处都是摆着小尾巴的蝌蚪,我们都养过蝌蚪,也都玩过在沉积了一层黄泥的河滩筑水坝修城堡的游戏。在河边开挖一条小水渠,把水引到几米外的河滩,再圈起一个小水坝,捉很多蝌蚪放进去养着玩。或者在玻璃瓶里养几条放在家里,看着它们慢慢长出两条腿,再长出两条腿,而小尾巴则从长到短直至完全消失,终于有一天,小蝌蚪变成了不只会游泳还会跳远的青蛙。很多孩子还能辨别不同种类的蝌蚪。
那时候孩子们的玩具不在商店里,而是要自己去寻找去制造的。河里还有一样可以玩的宝贝,就是那些光滑的五颜六色的卵石。每个孩子都会去捡漂亮的石头,颜色亮丽的,形状特别的,有各种花纹和图案的,捡回来浸在水盆里,比比看哪一枚更漂亮。这些被当做收藏的石头,经常会被新的更漂亮的石头淘汰。孩子们都会在家里藏一些自己喜欢的、经过无数次筛选留下来的石头。节假日里,那些从外地回来的亲戚,也会跟着小孩子到河里捡几枚石头带走,说是要点缀鱼缸或盆景。
小城的街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小水房,每个小水房都有一个专门放水的人,大家都在水房前排队挑水。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的水房温度太低,水管被冻住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到河里挑水吃。河面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大家就想办法凿开一个比水桶直径略大的圆形的冰窟窿,用扁担的铁钩子钩着水桶,从冰窟窿里打水。
而在不远处,孩子们正三三两两地比赛滑冰车。冰车是父母帮着动手做的,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木筏,下面嵌着两根平行的钢锯条,靠着金属与冰面的摩擦力可以快速前进,这是北方孩子最普及的一种冰上运动。小孩子或坐或蹲在冰车上,双手各握着一根铁杵,只需在冰面一点,就可以飞速地向前滑行。也有年长一些的,穿着冰鞋,弓着腰,背着手,优美的姿势像是掠过冰面的鸟儿。有一年冬天,这条河上还举办过一场地区级的冰球赛,热闹的场景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年中只有正月初一是禁忌挑河水的,因为这一天河里的龙都要出来,人们要回避。如果有人去挑水,就可能把龙挑回家里。据说有人不信老人的话,坏了这条规矩,果然大年初一的晚上,一家人熟睡到半夜的时候,那条龙就从水瓮里出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结果当然是这家人被折腾了个够。
围绕这条河,还有一个古老的风俗。五月端午节的清晨,每个人都要到河里汲水洗脸,而且,在洗脸之前绝不可开口讲话。所以,这一天早上,虽然家家户户厨房的大锅里都是煮了一个晚上的粽子,粽叶的清香已经弥漫了整个小城,但没有人先去尝一个解馋,年轻的挑着桶,年少的提着壶,男女老少都拎着洗脸巾,一个个神情严肃地往河边赶。有早早就洗过了的,已经一手挟着从河对岸采来的艾蒿、一手提着水回来了,便要逗着正往河边走的人说话,那赶着去洗脸的人紧紧抿着嘴巴,像不认识对方似的,埋着头快步走了。常有已经洗过脸的小孩子,专门守在路边等着招逗小伙伴说话。在端午节的大清早,看着一个个硬憋着不言不语甚至也不敢笑的大人小孩,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等洗了脸,采了艾,然后,粽子端出来了,一家人才大声说笑起来。
开春后,树枝才泛青,河水刚不冰手,就有人到河里洗衣服了。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不论午后还是傍晚,河里除了流水的叮咚声,就是女人们的欢笑声。孩子们放学回来了,问母亲在哪儿?听到的回答总是“去河里洗衣服了”。偶尔也会发洪水,人们就等着,相互问询“河开了吗?”,最多不过三五天,河水就澄清了。也有人等不到河开,就端着脸盆提着篮子到小河里洗衣服了。
好像是专为沿河人家而来的,清涧河的河床,一截宽一截窄,宽处河水清浅,卵石裸露,方便浣衣,窄处河水深幽,河底平坦,适宜游泳。因为门口有一条蓝色河床的河流,清涧城的人多半会游泳。
在河床宽的地方,水流缓缓,水底铺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卵石,随便找块光滑的大石头坐下,再找块平整的薄石片当搓衣板,就可以洗衣服了。如果怕正午的太阳太毒,就去早一点,占一个阴凉的位置。要知道,清涧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是一条从岩石上流过的河流,她日复一日温柔地凿开了坚硬的岩石,下切到深深的河床,于是,两岸青青的岩石半包着河水,形成天然的屏障,可以遮阳。坐在阴凉的石岸下,赤脚浸在水里,河水痒痒地缠绕着小腿,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夏天里,有些女人天天都要寻几件衣裳去河里洗,或者是想跟邻居姐妹拉家常,或者是在家里生了闲气,到河里洗洗头发,吹吹凉风,想想心事,散散心。
如果是傍晚去,天色暗了,河上凉快了,河里人少了,很恬静。听着流水和卵石击打出叮叮咚咚琴声一般的乐曲,还有偶尔的蛙鸣,真是美妙。在有月光的晚上,一个女人伏在河边洗衣,不时抬起一只纤细的手,拢拢散在额前的头发,河水和卵石都在那里闪闪烁烁,像是一河的宝石,那不是画,而是一首诗。
几十米的浅滩过去,又是一段较窄的河床,齐胸深的水,坚实的青石河底,像是天然的游泳池。一般是母亲在那边洗衣服,孩子在这边耍水,过一会儿,那边就有人喊一声,这边也有孩子应一声,喊的人就放心了,继续在青石板上搓洗着。
女孩子长到五六岁就会自己去河里洗小件的衣物了。记得刚开始洗衣服时,是在祖母或母亲的身旁,找一块小的光滑的石头坐下来,打很多的肥皂,狠劲洗自己的小手帕。再后来就搜罗了家人的内衣袜子,端着小脸盆,借着洗衣的缘由,跟着小姐妹去深处耍水。谁也没有泳衣,都穿着随身的小背心短裤,小姑娘站在石岸上,就像站在跳台上,捻着鼻子,“咚”一声扑进水里,像条鱼一样滑滑溜溜地游开了。
清涧方言把游泳叫“打澡戏”,蛙泳是“钻石岸”,仰泳是“打背水”。邻居或同学里有很多身手好的,样样都会。我因为体质差,运动方面总是落在小伙伴的后面,即便这样,也常常跟着大点儿的孩子,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还有游泳,都会一点儿,如果打比赛,还可以做个替补的角色。
常常是女孩们在这边玩,男孩们在几十米开外的另一个深水处玩,互相能看得到,但不会认出人来。
那时候已经懂得怕羞,从水里出来是要换干衣服的,那隐蔽的凹进去的石岸,就是我们的更衣室,即便距河岸十来米就是大路,大路上人来人往,躲在石岸下的小姑娘也是绝对安全的,一边换衣裳一边还在叽叽喳喳地争吵。
耍水也不是小孩儿的特权。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大人们歇息了下来,他们坐在院子的石床上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女人们互相问询着:咱们也去河里洗洗?男人们便抢着应:那我们也去,你们在上游,我们在下游,给你们照个怕,壮个胆。于是出门喊一声,街坊邻居男男女女十几二十个就相约着一起下河里了。
一般上到中学的女孩儿,就不会大白天耍水了,只有在晚上的时候,跟着母亲或姑姑婶婶到河里撒撒野。晚上玩也有特别有趣的事,在夜晚的水里,皮肤特别白净的女人,会比白天更耀眼,大家会戏称这是一个“二百五”的大灯泡,照得满河亮。常常正在互相打趣,一辆汽车开着大灯从岸边公路上驶过,河里一下子明晃晃的,女人们顿时尖叫着一齐钻到了水下……
雨
黎明时分,被嘈嘈切切的雨声吵醒了。那雨滴,敲打着瓦檐,密密的,脆脆的,像无数的珠子落下来。瓦片的凹槽处,帘子似的房檐水倾泻下来,不时地溅在倒扣在石床上的铁皮水桶上,叮叮咚咚的,于是,很倦怠很温柔地醒来了。
这是童年的某一个下雨的早晨。
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吧,近来,我常常会有幻听的情况发生。早上,半睡半醒的时候,会听到清晰的雨声,甚至能感觉到那种湿润的、新鲜的味道。拉开窗帘,看到的却是白朗朗的天、干梆梆的地,便要暗暗叹一口气。
那天,父亲在电话中说,家里的几间老房子又漏雨了,等天晴了,得请人彻底翻修房顶,把旧的瓦片房顶换成混凝土楼板。
其实这么多年来,每到秋天,我总在担心家里的老房子。几乎每年的雨季,老房子都要漏雨,已经请人重新铺过几次房瓦了,都没有大的改善。
其实我的心里,是恋着那用一页页瓦片连缀成的屋顶,要是掀掉瓦片、盖上混凝土楼板,房子的样子就不会那样鲜活生动了,那雨滴,落在房上,也不能够发出那样独特的动听的声音了。

我喜欢雨的声音,喜欢雨的味道,喜欢雨的颜色,喜欢那种清清凉凉的稍微有些暗淡的雨的感觉。
也不是所有的北方人都喜欢雨吧,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雨是和阴冷、潮湿、泥泞联系在一起的。
但故乡的雨是不一样的。在我的记忆中,雨天是安静的,明亮的,雨天是干净的,清爽的。
小的时候,我喜欢蜷在被窝里听雨声。趴着石板炕沿,看祖母把门帘挑起,把抽窗拉开,清新的雨的味道和香甜的土腥气便飘了进来,我会在那样的气味中迷醉。就因为雨中的土香味太特别太诱人了,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会偷偷地用指甲抠一点墙缝土来尝,当然,吃到嘴里可并不香甜,只能感觉到牙碜得慌。
院子的屋檐下石床上总是晾晒了辣椒、豆角、红枣和生了小虫的米面什么的,还有一坛正在发酵的豆豉,雨来了的时候,祖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收拾那些吃的东西,我也会跟着出去,能搬回来的就搬,搬不回来的也要盖上遮雨的物件。初来的雨滴愈来愈密地砸在头上,一边给祖母帮忙,一边体会那种跟雨赛跑的抢收的紧张,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孩子的乐趣啊。
雨终于下大了,先是街上人声嘈杂,行人仓惶奔跑,只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雨的声音。大家都躲在屋子里,有的默默地看雨,有的去忙手里的活儿。我坐在窗下,看玻璃上的雨花,看院子里越积越深的水。地面的水和继续落下的雨溅起一串串的水泡,我们把这种下雨天的水泡叫“送饭婆婆”, 源源不断的送饭婆婆哗啦啦地流向前院左侧角上的排水口,很是壮观。
我喜欢在小雨的时候,一个人上街溜达,不用打伞,仰着脸在细细的雨丝里,淋着,欢喜着。略淡的天空,不炫目也不灰暗,细柔的雨声,衬出了一片安静,像缓缓展开了淡淡的水墨画。
那时候,雨伞还不是人人必备的日用品,雨天去上学的孩子,遮雨的用具五花八门,有草帽,有雨衣,也有的用大塑料袋折进去一个角,自制一个雨披戴在头上。小孩子打伞似乎是没有的。我家里那时候好像只有三把伞,祖父祖母有很大很坚实的可以当拐棍使的黑布伞,父亲有一件深绿色雨衣,似乎是军用的那种,我们姐弟都是透明的塑料雨衣,而母亲则有一只非常漂亮的草绿色油纸伞。雨大起来的时候,撑着母亲的草绿色油纸伞,跑到院子里,旋转着伞柄,看雨滴在离心作用下飞溅。。。。。。
在外面突然遇到倾盆大雨,即便穿着雨衣,那风也会把雨水倾倒在身上,于是,顶着风冒着雨,像落汤鸡一样狼狈地跑回家来,浑身瑟瑟发抖。一进门赶紧换下湿衣服,然后被祖母用大被子包住,坐在热炕上,再喝点姜汤或热水,那就是暖暖的家的滋味啊。
雨水还有很多用途,下大雨的时候,家里人会把水桶、脸盆甚至锅子都放到院子里接雨水。祖父告诉我们,雨水可以入药可以沏茶,但祖母却说,城里的雨水是不能吃的,因为人家都烧炭,雨水里有烟毛,味道不好。接来的雨水是用来洗漱的。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有时候太阳还红红地照着,雨却大颗大颗地洒落了,我们叫这样的雨是“太阳雨”,有人纠正说应该是“退云雨”。有时候前街大雨滂沱,后街阳光灿烂,真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跟着雨锋跑,居然能看到地上有一条清楚的干湿分界线,很是奇妙。有时,半夜里雨来了,祖母立马起床,头顶着玉米秸编的盖盖,去给露天的灶台盖篷布,出门了才发现,在院子东西两边的石床上,我的父亲和堂叔父一边一个正睡得香,旁边的窗台上还亮着玻璃洋灯呢。天热的时候,他们俩经常会在院子石床上睡觉,睡前还都要看书,所以各人都带一盏洋灯。
秋天是连阴雨的季节,每年里总有那么十多天,大雨小雨绵绵不绝,窗户纸被雨洗烂了,东西瓦房开始漏雨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听到远处“轰”地一声,不知谁家的院墙坍塌了。祖母开始祈祷:这雨,该停了。
街上,老店铺的阔屋檐下,有挑了箩筐叫卖水果的农民在躲雨,这个时候披了雨具,踩着石板街面清清流淌的雨水,跑到人家的屋檐下采买水果,必定很便宜的,而且,那淋了雨的时鲜瓜果更加诱人。

落在屋檐的雨,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多年前初秋的一天,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我像一滴雨珠,来到这个世界。祖母说,那一天是天上的日子。
是因为在雨季出生,所以才喜欢这绵绵的雨吗?
我记忆中的小城,近三十年来已经脱胎换骨、面目全非了,我的家在前不久的城市改建中已经夷为平地,不久后将要竖起高楼。我的清涧河,据说已经不能洗衣了,自然更不能饮用不能游泳了。近些年,雨水也逐年减少,偶尔那么一年,生日的这一天,等了一天都没有落一滴雨。
这些变化让我很失落。
经常会梦到那座城,那条街,那条河。梦到下雨天赤着脚奔跑在石板街上,梦到雨滴敲打着瓦檐的声音……
那些美丽的记忆啊,应该会存留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心里吧。
——选自王馨散文集《故城故人——一个陕北县城里的家族记忆》



 发布日期:2022-09-12
发布日期:2022-09-12  点击量:
点击量: 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